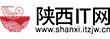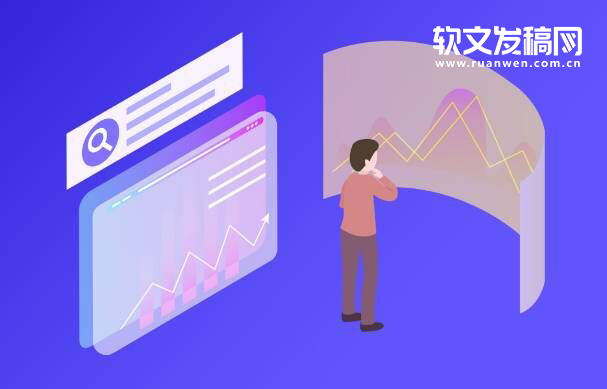自从感到身边的一切逐渐变得陌生,我就开始逃避现实;所实施的具体方式,便是在白天睡觉。这么做的好处和坏处都很明显:好处是时间会过得很快,就像玩视觉小说游戏的时候按下跳过键一样;坏处是会落得个“朽木不可雕也”的评价,而且夜晚不见得就比白天好过多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的眼睛适应黑暗的速度越来越慢,最后甚至到了近乎失明的程度;我知道我这是患上了“夜盲症”,好在它并不会太影响生活,只是晚上去客厅找水喝的时候有点麻烦而已。
这种安静如死水般的日子大概过了有两个星期,我又觉得无聊起来,想要把夜晚的时间也一并抛弃。办法有两个,一是干脆一直睡下去,二是顶着伸手不见五指的视野找点事情干。永远沉浸在梦里显然不太现实,于是我只好开始练习在黑暗中找到向前进的平衡感。最初的几天,我只敢走到卧室门口;对面居民楼的灯光从窗户透过来,给屋子里的东西打上了模糊的轮廓。慢慢地,我能够走出房间,靠着触觉和记忆在客厅里行动自如了。
但我不会满足于此。在又花了一天做好心理准备之后,我在午夜蹑手蹑脚地打开大门,从家里溜了出去,动静之轻微,甚至没有唤亮楼道里的声控灯。
 (资料图)
(资料图)
黑暗立刻张开大嘴吞了过来,像是要将我整个咽下;我紧靠着墙壁,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过了一会儿,我确定没人从睡梦中醒来,便试探性地拍了拍手。然而我的力道控制得并不精准,弄出了很明显的声响,又没能成功把灯点亮。我随即紧张起来,想要用咳嗽掩盖过去,又发觉咳嗽的声音可能比拍手还大,只好硬生生地把到嘴边的那口气憋了回去。我回想着平常躺在床上时听到过的那些半夜才回来的醉汉是怎么喊亮声控灯的,越是想着越有一股破罐子破摔把所有人都叫醒的冲动。最终,回忆中别人的喊声和我的声音重合在一起,我没来得及阻止自己,就已经张开了嘴。
“啊。”
灯没亮。
“啊!”
楼道里如同突然升起一盏太阳。
我完全暴露在灯光下,条件反射般地伸出手挡在眼前,却发现掌心感受不到任何温度。我明白我还在紧张,于是强制性地深呼吸了几下,一点一点地观察着再熟悉不过的家门口。等到声控灯自动熄灭,我才缓慢地往前挪着步子。整个下楼的过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艰难,在一只手紧抓着楼梯扶手的情况下,判断下一节台阶的距离是很容易的事情。
终于,我站到了敞开的单元楼大门后面。微弱但柔和的路灯将余晖浅浅地涂在门口,那是一种既能让我看得清楚又不至于令我感到炫目的亮度。我走到门外,路灯的光照范围肉眼可见,一个个银白色的光球在路边排成一排;在那之外的地方仍是漆黑一片,楼房和树木草坪相互交融,从中偶尔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想来应该是觅食的流浪猫。
好吧,我对自己说道,我出来了,现在我要往前走,先走到这条路拐弯的地方再——
还没等我迈出下一步,远处的天空就被点亮了。我看不清那是什么,它比飞机更快,比流星更明亮;直到那团光焰变得愈来愈大,点燃了半空中的云,我才意识到接下来可能会发生怎样的事情。那东西径直坠向地面,爆炸产生的火焰让半边天空变成了白昼;几秒钟之后,一声巨响传来,周围一些住户家里的玻璃应声碎裂。路灯在眨眼间全灭了,然而不用借助路灯,仅凭远处升起的火球,就能让我看清楚眼前的一切。
天空中翻滚着的黑烟莫名其妙地吸引着我。我站在原地,忘记了要转身逃走。身后的居民楼里挨家挨户亮起灯,有人跑到楼下,同样震惊地看着坠落的方向。消防的警铃声由远及近,混乱随后而至。
我因为偷跑出去挨了顿骂。第二天,电视上放出新闻,一架无人机坠毁在了附近的公园;但网络上的声音截然相反,有人把现场的照片发了出来,就算那东西被摔得只剩半边,模样也更像是一艘会出现在影视作品里的、来自外太空的飞船。一时间言论四起,警戒线拉到了小区门口,那座公园也被禁止进入;直到数天之后,第一个上当受骗的人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整件事又开始往另一个性质转变。当那位中年妇女还担心着自己的儿子会不会被外星绑匪撕票的时候,人们已经在阴谋论里猜测下一场世界大战会不会就这样爆发了。
再后来,这次事故被定性为一次纯粹的意外;所谓的飞船其实是用来监测气候变化的先进仪器,所幸事发深夜,并没有任何人因此受伤。几辆卡车运走了那块残骸,公园里围起了一片进行修缮的施工区域。在有条不紊地维修了两星期后,公园焕然一新,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与此同时,距离我和那位天外来客第一次接触,已经过去了好一阵子了。
我没有因为挨骂而停止在夜间的活动,甚至就在那次坠落发生的第二晚,我仍在小区里游荡。我迷恋上了这种把已知变为未知的感觉,胆子逐渐大了起来,每次出门的距离也越来越远。我走出了小区,靠着路灯的帮助穿过马路,踏进了公园的大门。
午夜时分,公园里是没有任何人工照明的;但即便如此,我却惊讶地发现这里的人比我想象中的要多很多。那会儿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还没被拉走,有不少人偷偷地越过挡路的水马,围着它拍照。我本来也想去看看,奈何摸不清具体的方向,只好沿着道路的边缘慢慢地走着。然而在不知不觉间,我走上了一条通往人工湖的小路;脚下传来的触感逐渐从水泥的坚实变成了泥土的松软,正当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准备走出下一步时,有人开口拦住了我。
“你再往前,就要走到湖里去了。”
就像是为了证明他的话似的,不远处传来溅起水花的声音——某条熬夜的鱼在水面上翻了个身。
“多谢提醒。”
“你遇到了什么伤心的事吗?”
“不……不,没有,真的。”我有些意外,“为什么这么问?”
“我看你直勾勾地往湖里走,还以为你要做什么傻事。”
我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但那里只有一大片黑影。他完全融进了地面和树丛当中,我无法看清他的样貌。
“我只是眼睛不太好。”我说道,“一到晚上,就看不清楚东西。”
“原来是这样。”
我们不约而同地沉默了一会儿。
“我记得这边离那台坠毁的玩意儿有些距离。你不是来看它的吗?”我问道。
他没有第一时间回答我,这让我以为他已经离开了;结果他突然开口,吓了我一跳。
“那对我来说就是‘伤心的事’。”
“嗯?为什么?”
“因为那艘飞船是我的。”
我的大脑没有第一时间分析处理这句话,因为我自然而然地把它当成了一句玩笑。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便继续说了下去。
“我在进入大气层的时候有些操作失误,再加上它本身离报废也不远了,所以我不得不提前弹出座位,丢下它逃命。等我想让它落在无人区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还好这里是座公园。”
我觉得我可能是遇上骗子了。接下来,他是不是要以维修飞船或者讨口饭吃的理由管我借钱?最坏的结果,就是从身后的树丛中窜出几个人,进行一场真正的绑架。
“啊,这样啊,哈哈。”我飞快地检索着能用来脱身的借口,“那真是可惜——我是说,那还真是挺幸运的。这么晚了,我得回去了,有缘再见。”
我转身向后跑去,顾不得能否看清脚下的路。他不是骗子,就是疯子,反正不会是外星人。每天来公园的人那么多,怎么偏偏让我遇上这种事?我一边想着,一边寻找有光亮的地方。
但是他呆在湖边做什么?这个时候,那地方几乎没有人会去。除非是一路跟着我……我越想越害怕了。
第二天,我专门放弃了下午的睡眠,又凭借着记忆中的方向感回到了昨晚的位置。四下无人,只有几条离群的锦鲤在水中游着;一股不真实感袭来,我开始怀疑昨晚的对话只不过是发生在梦境中的事情。
我没找到能证明更多东西的线索,便前去观看搬运那块残骸的现场。周围有许多新闻社来的人,无数长枪短炮对准被吊车吊在半空的金属骨架,像是部署在地面的防空力量。人群散去,我从另一条路走出公园,在路上仍能听见很多讨论的声音。我没有心思仔细听,昨晚的对话还在脑海中回响。
“……因为那艘飞船是我的……”
事到如今,我反倒有些希望他说的都是真的了。这几天我总是在期待一些听上去就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在大半夜逛公园,比如说在逛公园的同时顺便结识一位外星人。
于是当天夜里,我再一次返回到那湖边的角落。还没等我走近,就又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你又来了。”他的语气有些惊讶。
我突然有些手足无措。他的惊讶是合理的,毕竟我没有连续两次都走错路的可能,也没有专门回到这里的理由——除了那近乎找乐子一样的心态,但真要说出来,我仿佛就会成为某种心态很恶劣的无业游民。
“呃,是。”我挠了挠头,“今天我看到他们把那个……那艘飞船给拉走了。你不是说那是你的东西吗?”
“我也没有办法。”他叹了口气。
“不试着挽留一下么?说不定还是有修好的可能的。”
“这里不在飞船的售后服务范围内,修理工赶不过来;再加上我其实觉得没有修好它的必要,所以就……”
他流畅且自然地说着,似乎默认了我能听得懂这些话。
“没有修好的必要?为什么?”
在他开口之前的几秒钟,离脚边一步之遥的水面泛起淡淡的涟漪;微风拂过,身后的树丛沙沙作响。有什么东西在周围冒了出来,悄无声息,渗进空气当中,与他即将说出的话一起凝成汹涌的情绪,让我提前感受着。半个星系在湖面旋转,我诧异地遏制住夺眶而出的泪水,不知道这股悲伤从何而来。
“我就快死了。”
他沉默良久,接着说道:
“我们的种族从有意识起就会知道自己的死期。但我在到处旅游的时候不小心把它忘了,等我想起这件事去查的时候,发现时间已经不够让我回家了。我总不能死在飞船上,让它变成太空垃圾,只好就近选择了在这里降落。”
“结果出了意外。”他自嘲地笑了一声。
我没有接话,过往的经验并没有教会我遇到这种情况时该说些什么。但一声不吭显然不太礼貌,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试探性地问东问西。
“那……你还剩多少日子?”
话一说出去我就被自己蠢得后悔了,好在他似乎不太在意。
“明天。”他说道,“明天的这个时候。”
摆在眼前的情况有些复杂。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我面对的是一个生命走到尽头的外星人;倘若他只是一个入戏太深的普通人,那听他的意思,怕不是明晚就要自我了断?我该想办法阻止他吗?
“我好想回家啊。”他念叨着。
“你们没有那种技术吗,什么‘虫洞’、‘传送门’之类的?”
他摇了摇头:“那听起来简直是魔法。”
我努力地寻找着下一个话题。
“你的家乡,是什么样子?”我问道,“和这里很像吗?”
他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像,但也不完全像。那里有很多的海,陆地只有一小块。所有人都是从海里出生的,也必须要在海里死去。”
我突然非常好奇他究竟长什么样子,但刻意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去看未免也太冒犯了。
“在海里死去……可这里是内陆城市,根本没有海啊?”我意识到有哪里出了问题,“离这里最近的海岸线有将近一千公里,你赶得过去吗?”
“我个人对‘海’的定义比较宽泛。”他说道,“如果海洋只是一大坑水,那就太无趣了。你见过海吗?”
“我只见过一大坑水的那种。”
我在临海城市四业上过几年学,对大海的记忆还停留在湛蓝、广阔和远处的许多大船。但我不属于那里。无论是在白天看到在沙滩上嬉戏的人群,还是在晚上听到对着大海说出的约定,都让我觉得陌生,仿佛那不是我亲身经历,而是一场看了半途的电影。
“海的位置,我写在这里了。”他折断一截树枝,身旁传来划过泥土的声音,“如果你有兴趣,在明天的夜幕降临之后,就能在那里看到我。”
“会很远吗?”
他没有回答,应该是离开了。我又在原地呆了一会儿才回家,但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睁着眼睛目睹了拂晓的到来。
他在地上写下的是一处经纬度的坐标,用地图查看,位置指向了城市北边郊区的山脚下,那个面向公众开放的免费的小景点。不知道是何种心理作祟,我用脚抹平了地上的痕迹,就好像那是什么不能被别人知道的藏宝地似的。
我没有给自己“去”和“不去”的选择,我就是为了这种事情才天天在半夜出门的。当天下午,我找人借了一辆旧自行车,一路骑到了山下的景区入口。夕阳挂在天边,似乎完全沉没到地平线下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视线随着时间明显地模糊起来,好在这片地方到了晚上就是周围居民散步的场所,路灯比公园里的还要亮。我坐在自行车上等待着,天空的色调越来越深,在某颗星星的光芒变得突兀的那一刻,我看了看表,现在是晚上八点十分,距离昨晚他亲口预言自己死亡的时间还有将近五个小时。
突然,周围的光线全部消失了;在广场上的人发出阵阵惊呼,猜测着是不是供电线路出了问题。等到最后一束手电筒发出的光也走远了,我听到身后传来他说话的声音。
“板块运动对于宇宙间任何一颗星球来说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数亿年间,地面上升下降,海水时进时退,又经过百万年的锤炼,最后形成了这种……凝固的巨浪。”
他说话的速度比以往都要快些,语气里带有隐约的狂热。
“你能想象吗?如果把它们看做深邃的海沟,那我们现在站着的地方大抵就是海面;再然后,地下就是曾经的陆地和天空。”
我摇摇头:“对我来说,这就是一座普通的山而已,甚至和其他的山比起来,它也算是毫无特点的那种。”
“你每天都能看到它现在的样子,自然会习以为常。”他说道。
“难不成你见过好几亿年前到处都是一片汪洋的地球吗?”
“在前人留下的旅行手记里看到过照片。”他又是很自然地说着一些不得了的话,“这也是我来这里的原因之一。要不是我忘了今天就得死,还把飞船摔了,我肯定会留在这儿,把最著名的山峰都爬一遍。”
相比于远古时期地球就有外星人造访的事情,我更在意一颗全是水的星球有什么值得旅游的地方。
“我们走吧。”他说道,“虽然在最后做不到像计划好的那样顺利,不过随机应变一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凭借着感觉向登山的台阶走去,而他形同鬼魅,连脚步声都没有。正当我准备扶着岩壁往上走时,我又忽然想到了什么。
“广场上的灯刚才全灭了,这爬山的路也漆黑一片,是你干的?”
“当然不是。”他说道,“只是一次巧合罢了。”
我接受了这个解释,继续往前走着。我头一次觉得夜盲症是相当麻烦的毛病,这座山头并不高,平时我花一个小时就能爬到顶;而现在我每向上一个台阶,都要浪费好几分钟的时间来确认自己有没有走到悬崖边上。那个外星人也指望不了。他好像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管我,而是径直往上冲去;不过这也能理解,如果他不是骗子,还有几个小时他就要死了,自然不能把爬山的过程作为最后一次旅行的重点。
我有些烦躁,思绪不受控制地到处乱飞。我想起在四业市上学时看到的海,那算得上是当地的标志之一;可我并没有对它产生更多感情,正如我没有对正在攀登的这座山有什么感情一样。那个外星人,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旅行的途中,即便如此还在为不能回家而遗憾不已;哪怕要死在陌生的星球,也要来到这几百万年前就已经干涸了的海洋,只是为了一种虚无缥缈的传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好像比我这个本地人还要重视这座山,以及那片我们都素未谋面的海。
爬了一半,我有些累了。这几天睡眠不足,再加上几乎无时无刻都在想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让我感到久违的疲惫。不过仔细一想,这些事情好像和我也没什么关系,是我自己非要凑上前来的。我靠着栏杆,抬头向上看去,今晚的天气也一如既往地晴朗,月光的存在渐渐明显起来,我的眼睛也开始缓慢地适应着黑暗。
越往上,山坡越陡,台阶越高。山顶的一尊雕塑反射着银白色的光,看到那个,就说明离登顶不远了。
“那是什么?”他突然在身旁发问,吓了我一跳。
“原来你一直在这儿吗!”我差点摔倒,扶住栏杆将身体稳住,“那是以前封矿时留下的,形状是一根弯曲的针,寓意是努力缝补被破坏的环境。”
“它有名字吗?”
“缝山针。”我回答道。
他没再说话,似乎又像之前那样往前走了。我想起自己小时候曾以为那个雕塑是用来接收外星信号的天线,莫名觉得有点好笑。要是他来得再早些,在我对一切的态度还不像现在这样淡漠时把飞船停在公园里,我又会是什么样子?
最后几节台阶修得很平整,我一口气跑了上去。这里和记忆中并没有太大差别:几乎和山下广场一样大的平台、被围起来的雕塑,以及能眺望城市全貌的视野。尽管现在已经是深夜,却还有一些建筑亮着灯;零星微光点在夜幕,与头顶的星空织在一起,看不清楚天际线在什么位置。
“我从来没有在这个时候爬过山。”我说道,“没想到这里夜晚比白天的光景还要漂亮。”
他还在沉默。我偷偷看了一眼表,离昨晚他说的时间还剩一个多小时。难以言喻的氛围弥漫在山顶,山下传来货车驶过的声音。
“你说得对,这里的确很普通。”他说道,“我在其他地方见过的山,要么奇形怪状,要么高耸入云。”
“你说的那种,地球上也有,只不过不在这儿。”我解释道,“我和你说过,这里毫无特点,只是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是一片大海。”
我听到摩擦地面的声音,他好像从地上捡起了什么。
“你觉得这儿行吗?”我问道,“作为……呃,作为你死去的地方?”
“我很满意,不如说这地方再合适不过了。”
“就算它这样普通?”
“我还能奢求什么呢?”他轻笑一声,“宇宙中葬身于传奇之地的冒险家有很多,可我并不是那样的人。最后的日子里还能见到曾经是海洋的地方,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剩下的似乎就只剩等待了。我并非什么只会找乐子的流氓,也没有背负着什么“见证一位外星人生命终结”的使命;事到如今,让我留在这里的理由,连我自己也想不出来。可我仍连续好几个晚上和他交谈,顶着夜盲症和没有照明的路爬到了山顶。就像我明明对四业市的海和脚下这座山没什么话可说,却依然在每每提及它们的时候,脑海中的画面都会鲜艳生动一样。
“差点忘了,我有个东西给你。”他递给我一个盒子,“权当是一份谢礼。”
“我什么也没做。”我摇摇头。
他没多说什么,我也顺从地接过了那个盒子。我把它打开,里面是一副眼镜。
“夜间专用。”他说道。
我摘下自己的眼镜,把那件礼物换上。视线穿过镜片的一瞬间,周围像是变成了白昼一样明亮。黑暗褪去,图像和色彩重入眼帘。当我扭过头,试图看清他的样貌时,发现他已经消失不见,原先站着的地方只有一片潮湿的水渍。那是属于他的海洋。
我在山顶又坐了一会儿之后,把那眼镜放回盒子里,摸着黑小心翼翼地下了山。等我走回山下的广场时,天边的颜色已经略微的明亮了起来;路灯不知道什么时候重新恢复了正常,附近的村庄传来公鸡啼叫的尖锐声响。
像是刻意赌气似的,我转过身,望向还处于夜晚中的山峰,对着它说道:
“这到底还是一件无聊的事。我对你的看法不会改变。”
而它始终保持着汹涌澎湃的姿态,回应我的只有那跨过亿万年间的沉默。
关键词: